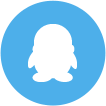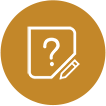世纪之交的回顾——析《红楼梦》“诲淫”、“非淫”之争
作者:张宗伟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终结,它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小说的优秀传统。尽管《红楼梦》问世的清乾隆前期距我国近代史的开端尚有近一个世纪,但作为时代先声的《红楼梦》已经有了文学近代意识的萌芽。遗憾的是,由于中国文学理论对小说的传统轻视和理论本身的“滞后效应”,使得《红楼梦》所体现的优秀传统和它所昭示的文学的近代意识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总结和阐发。及至清末民初,情况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清末民初是我国小说理论空前繁荣的时期。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理论把小说由“小道”提到了“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①]使文学批评的重心由传统的诗文移到了小说领域,但是梁启超出于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粗暴地否定我国古代的优秀小说,贬斥《红楼梦》等为“诲淫”之作。[②]梁氏此言一出,在清末民初的红学界和整个小说理论界引发了一场持久的争论。从1989年梁启超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直到1914年吕思勉刊出《小说丛话》,当时重要的红学研究者和小说理论家大都涉及了《红楼梦》“诲淫”、“非淫”之争。这为考察清末民初的小说理论提供了一个参照,通过透视那场“世纪之争”,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把握当时纷繁复杂的小说理论。
一、梁启超一笔骂倒《红楼梦》
尽管梁启超于1902年才正式提出“新小说”或“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欲改良政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③]但是他的“新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旧小说”诲淫诲盗的批判却始于戊戌维新前后的1897年。
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连载的《变法通议·论幼学》中将古代小说斥为:“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莫或知”,已初现“诲淫”说端倪;1898年《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则表述得更为具体:“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淫诲盗两端。”否定了《红楼梦》、《水浒》等古代优秀小说。
梁启超认识到小说革命在启蒙运动中的突出地位,认识到小说在觉世新民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对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皆有“不可思议”的支配力,因此他把小说推崇为“文学之最上乘”,但他在对待古典小说时却将孩子连同脏水一起泼掉了。《红楼》、《水浒》是“文学之最上乘”的小说的“最上乘”,他却简单地痛斥为“诲淫诲盗”,“隐溺人群”,“含有秽质”,“含有毒性”,这是梁启超“新小说”理论的最不成熟之处。它的出现有着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终结,它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小说的优秀传统。尽管《红楼梦》问世的清乾隆前期距我国近代史的开端尚有近一个世纪,但作为时代先声的《红楼梦》已经有了文学近代意识的萌芽。遗憾的是,由于中国文学理论对小说的传统轻视和理论本身的“滞后效应”,使得《红楼梦》所体现的优秀传统和它所昭示的文学的近代意识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总结和阐发。及至清末民初,情况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清末民初是我国小说理论空前繁荣的时期。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理论把小说由“小道”提到了“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①]使文学批评的重心由传统的诗文移到了小说领域,但是梁启超出于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粗暴地否定我国古代的优秀小说,贬斥《红楼梦》等为“诲淫”之作。[②]梁氏此言一出,在清末民初的红学界和整个小说理论界引发了一场持久的争论。从1989年梁启超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直到1914年吕思勉刊出《小说丛话》,当时重要的红学研究者和小说理论家大都涉及了《红楼梦》“诲淫”、“非淫”之争。这为考察清末民初的小说理论提供了一个参照,通过透视那场“世纪之争”,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把握当时纷繁复杂的小说理论。
一、梁启超一笔骂倒《红楼梦》
尽管梁启超于1902年才正式提出“新小说”或“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欲改良政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③]但是他的“新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旧小说”诲淫诲盗的批判却始于戊戌维新前后的1897年。
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连载的《变法通议·论幼学》中将古代小说斥为:“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莫或知”,已初现“诲淫”说端倪;1898年《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则表述得更为具体:“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淫诲盗两端。”否定了《红楼梦》、《水浒》等古代优秀小说。
梁启超认识到小说革命在启蒙运动中的突出地位,认识到小说在觉世新民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对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皆有“不可思议”的支配力,因此他把小说推崇为“文学之最上乘”,但他在对待古典小说时却将孩子连同脏水一起泼掉了。《红楼》、《水浒》是“文学之最上乘”的小说的“最上乘”,他却简单地痛斥为“诲淫诲盗”,“隐溺人群”,“含有秽质”,“含有毒性”,这是梁启超“新小说”理论的最不成熟之处。它的出现有着
点击展开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