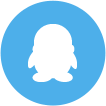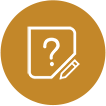研究作家与解析作品——就《红楼梦》“自传说”问题谈
作者:袁世硕
【内容提要】
:“新红学家”考证出曹雪芹家世生平的一些真实情况,并同《红楼梦》联系起来,拨开了“旧红学家”比附、索隐的迷雾,这对了解《红楼梦》来说是一次飞跃,功不可泯;但后继者沿着其导向,尽力坐实其说,把《红楼梦》当作曹雪芹的生活实录,这又显示出“自传说”谬误的一面。《红楼梦》研究,固然应以对小说本身的解析为主,但由于小说是曹雪芹依据自己的生活经历虚构而成的有实有虚的生活图像,因此,若无视对曹雪芹的研究,同样有可能对《红楼梦》本身产生误解。所以,文学研究的正确方法应是将研究作家与解析作品结合起来,而研究作家不能远离解析作品这个中心,目的仍是为了解析作品。
读书要知人论世,古人早就提出了这个命题。从作家的生平经历、思想性情来解析其作品,也早就成了一种常用的、甚至可以说是习惯性的研究方法。中国如此,外国亦然,称作传记式文学批评。可能是由于受传统的经学、史学的影响较深,在中国表现得更为突出,至今在文学史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对考证作家的生平事迹,怀有浓厚的兴趣。
本世纪以来,这种古老的研究方法受到了挑战。西方出现了几种文学批评流派,强调文学的本体批评,认为文学批评主要关注的应该是作品,对作家生平思想的研究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因为那样会使注意力从作品本体转向作者,对作品的解析变作对作家意图的探究,而探究作家的意图往往是不可靠的,即便是可靠,那也只是说明了作品的起因和创作过程,还没有触及作品的本体结构,还不能算是对作品本体的批评。在中国,一些青年文学研究者也久已对文学史研究中充溢着考证性的研究颇有意见,西方的这种理论的传入,就使他们更为不满了。
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须要做些认真的研讨。这里我想走个捷径,就是只就《红楼梦》研究中有争议的“自传说”问题做个举例性的讨论,虽然不可能很全面、深入,但也或许不无裨益吧!
自《红楼梦》问世200多年来, “自传说”一直伴随着它经历了那么长的并不平直的路程,看来好象是整整地转了两个大圈子。
第一个圈子是鲁迅先生勾画出来的。他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红楼梦》“自传说”的形成和被确定,做了这样的评述:最早是嘉庆初年,袁枚在其《随园诗话》里曾经约略地讲到,康熙间曹寅做江宁织造,“其子(应为其孙)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
【内容提要】
:“新红学家”考证出曹雪芹家世生平的一些真实情况,并同《红楼梦》联系起来,拨开了“旧红学家”比附、索隐的迷雾,这对了解《红楼梦》来说是一次飞跃,功不可泯;但后继者沿着其导向,尽力坐实其说,把《红楼梦》当作曹雪芹的生活实录,这又显示出“自传说”谬误的一面。《红楼梦》研究,固然应以对小说本身的解析为主,但由于小说是曹雪芹依据自己的生活经历虚构而成的有实有虚的生活图像,因此,若无视对曹雪芹的研究,同样有可能对《红楼梦》本身产生误解。所以,文学研究的正确方法应是将研究作家与解析作品结合起来,而研究作家不能远离解析作品这个中心,目的仍是为了解析作品。
读书要知人论世,古人早就提出了这个命题。从作家的生平经历、思想性情来解析其作品,也早就成了一种常用的、甚至可以说是习惯性的研究方法。中国如此,外国亦然,称作传记式文学批评。可能是由于受传统的经学、史学的影响较深,在中国表现得更为突出,至今在文学史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对考证作家的生平事迹,怀有浓厚的兴趣。
本世纪以来,这种古老的研究方法受到了挑战。西方出现了几种文学批评流派,强调文学的本体批评,认为文学批评主要关注的应该是作品,对作家生平思想的研究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因为那样会使注意力从作品本体转向作者,对作品的解析变作对作家意图的探究,而探究作家的意图往往是不可靠的,即便是可靠,那也只是说明了作品的起因和创作过程,还没有触及作品的本体结构,还不能算是对作品本体的批评。在中国,一些青年文学研究者也久已对文学史研究中充溢着考证性的研究颇有意见,西方的这种理论的传入,就使他们更为不满了。
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须要做些认真的研讨。这里我想走个捷径,就是只就《红楼梦》研究中有争议的“自传说”问题做个举例性的讨论,虽然不可能很全面、深入,但也或许不无裨益吧!
自《红楼梦》问世200多年来, “自传说”一直伴随着它经历了那么长的并不平直的路程,看来好象是整整地转了两个大圈子。
第一个圈子是鲁迅先生勾画出来的。他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红楼梦》“自传说”的形成和被确定,做了这样的评述:最早是嘉庆初年,袁枚在其《随园诗话》里曾经约略地讲到,康熙间曹寅做江宁织造,“其子(应为其孙)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
点击展开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