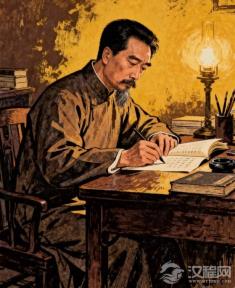心物交溶 文与道俱——苏轼文艺本质论
作者:李斌
论文关键词:苏轼 文艺本质 主体性 客体性 思想性 艺术性
论文摘要:苏轼对文艺的一个重要认识是,文艺是“外物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的产物,实际上说明了文艺作品是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这是苏轼从艺术生成论角度对文艺本质所作出的一个辩证的概括。苏轼对文艺本质的另外一个重要认识是,“文与道俱”,道文并重,实际主张文艺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这是苏轼从艺术本体论角度对文艺本质的认识。
苏轼既是宋代首屈一指的文学家和杰出的书画家,在诗、词、文、赋、书法、绘画等几乎当时所有的艺术门类中都有极高的造诣;又是颇多建树的文艺理论家,其理论思想对此后的中国文艺美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他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并结合前人和时人的经验之谈,对于文艺的本质、文艺的价值、文艺的创作与文艺的风格诸多间题提出了既独具特色又融汇贯通的认识.笔者以为,他事实上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艺美学思想体系,不过,他总体上系统化的理论思想,却散落于书简、题跋和诗文之中,后人免不了要去做一番级珠采玉的生夫。笔者在本文中只拟从他的理论著述里梳理出他关于文艺本质的一些重要看法,并期待能够抛砖引玉,从而共同推动对苏轼文艺美学的研究.
苏轼对文艺的一个重要认识是:文艺是“外物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苏拭《江行唱和集叙》:下引
论文关键词:苏轼 文艺本质 主体性 客体性 思想性 艺术性
论文摘要:苏轼对文艺的一个重要认识是,文艺是“外物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的产物,实际上说明了文艺作品是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这是苏轼从艺术生成论角度对文艺本质所作出的一个辩证的概括。苏轼对文艺本质的另外一个重要认识是,“文与道俱”,道文并重,实际主张文艺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这是苏轼从艺术本体论角度对文艺本质的认识。
苏轼既是宋代首屈一指的文学家和杰出的书画家,在诗、词、文、赋、书法、绘画等几乎当时所有的艺术门类中都有极高的造诣;又是颇多建树的文艺理论家,其理论思想对此后的中国文艺美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他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并结合前人和时人的经验之谈,对于文艺的本质、文艺的价值、文艺的创作与文艺的风格诸多间题提出了既独具特色又融汇贯通的认识.笔者以为,他事实上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艺美学思想体系,不过,他总体上系统化的理论思想,却散落于书简、题跋和诗文之中,后人免不了要去做一番级珠采玉的生夫。笔者在本文中只拟从他的理论著述里梳理出他关于文艺本质的一些重要看法,并期待能够抛砖引玉,从而共同推动对苏轼文艺美学的研究.
苏轼对文艺的一个重要认识是:文艺是“外物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苏拭《江行唱和集叙》:下引
点击展开查看全文
展开全文
APP阅读
特色专题
更多精彩推荐
文学指南
更多 >热门栏目
更多 >热门文章
更多 >
“抒情传统”说的再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史诗与抒情之争
文学杂谈
张爱玲的晚期写作:《小团圆》中的创伤记忆与叙事伦理
文学杂谈
“打工文学”的三重维度:阶级经验、身体叙事与身份政治
文学杂谈
“新笔记体”小说的当代流变:从孙犁、汪曾祺到阿城
文学杂谈
汪曾祺的“文人”与“民间”:论其小说中的士大夫精神与市井智慧
文学杂谈
莫言的酒神叙事:《红高粱家族》中的民间仪式与历史重构
文学杂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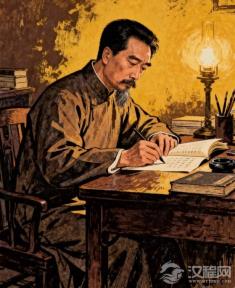
鲁迅的沉默与言说:《故事新编》中的历史寓言与启蒙困境
文学杂谈
王国维“境界说”的现代性潜流:以《人间词话》为中心的再阐释
文学杂谈
“抒情传统”说的当代回响: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抒情主义与史诗冲动
文学杂谈
“漫长的90年代”:市场经济转型与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及其终结
文学杂谈